Browse
棕櫚樹林一望無盡地在公路兩旁展開,這帶有熱帶風情的人造風景佔據了遼闊的視野。在穿越棕櫚樹林後,終於到達半島原住民(Orang Asli)的部落。
Kuala Lumpur:起點
我和Jeffery Lim(中文:林猶進)站在鵝嘜河(Sungai Gombak)與巴生河(Sungai Klang)匯流處,不遠處還有半夜在大樓上施工的(多數為)移工們和大型施工機具不停發出聲響—他正為剛抵吉隆坡的我介紹他所生長的這個城市開發的起點。華人、馬來人、印度人等各種不同族群,以河域為界居住在城市不同的區域。依據官方資料,馬來西亞歷史可上溯至千年,但其實吉隆坡是一個年輕的城市。 「這裡以前也有原住民,這裡開始有其他人過來以後,他們只好離開,不知道以前住在哪裡…」
Jeffery在我身旁像是自言自語地喃喃說著。他有華人的外表,從小接受馬來語與英語教育,在我們一起合作的計劃中,他透過自製相機做為探索認同概念的方法,延續去年我們一起完成有關台灣原住民族的影像,這次透過他的牽線,來到他位於馬來半島的故鄉,試圖與當地的原住民進行文化交流。這次我們主要會走訪上霹靂州庫內村(Kampung Cunex)的Temiar部落、雪蘭莪州Lanjan山旁特姆村(Desa Temuan)的Temuan族人、彭亨州雲彬Jemeri村的耶坤族,以及加厘島(Carey)布本村的瑪美里族(Mah Meri),但在拜訪第一個部落以前,我卻愁著自己連阿美族語都不太會,生命有大半時光在城市中度過,在阿美族背景裡我這個從外表到背景都嚴重漢化 的原住民,要與當地的原住民交流什麼文化?
Desa Temuan:香蕉樹上的女人

我1981年出生,1996年這裡開始開發,1997年我們搬進長屋,Saujana Triangle MK Land整個工程花費六年,我們大概在2000年以後搬到這裡。
住在吉隆坡郊區Lanjan山旁特姆村的Temuan族人阿努阿爾阿茲曼(Anuar Azman)告訴我:「我們來自Bukit Nanas(鳳梨山/咖啡山)那邊,就在吉隆坡塔那裡。」我想起昨晚開車經過的Bukit Nanas住宅區及兩河匯流處,旅伴介紹的吉隆坡城市風景。
特姆村就在離吉隆坡市區不遠處正在興建的高速公路旁。沿著公路開車過來,首先看到一個大型購物中心矗立在社區路口,再往下走是一座小清真寺,然後才抵達這個都市部落。社區裡有一棟公寓大樓,其他看起來是獨棟住宅,清真寺廣播的喚拜聲在部落裡一樣定時規律響起,部落裡也有不少人已是穆斯林。雖然看起來就跟一般住宅區一樣,事實上部落裡大部份都經歷過二、三次搬遷,並在政府的引介下,以喪失大片土地換來現在的生活。頭目Ismail bin Cat為我們解釋有關地名的由來:「Desa Temuan以前稱作Kampung Bukit Lanjan—lanjan是指那座山(指向不遠處的山丘),是malas(馬來文:懶)的意思。我們在這附近的山走來走去,累了就lanjan。」他所指的那座山,現在看起來像中間被劃開深深一刀,正在蓋出一條新的公路。事實上,在頭目Ismail的決策下,近20年前把整座山的土地賣給開發商,換來一些賠償金及現在居住的房子,也從此改變他們的生活。
Norlila是村裡少數還會傳統編織的人,他以傳統編織並用手機從Youtube上學習新的織法,依靠雙手做出各種藝品,攥些外快貼補家用。他大剌剌地向我們展示他的手藝,也表達他對不停迫遷與凡事要錢的生存感到疲倦。聊天過程中,Norlila提到一段讓我很感興趣的生命故事:話題始於他在院子裡種植草藥,是過去要上山才能採到的植物。因為山已逐漸消失,所以他試著在只有貧脊土地的院子裡種出草藥來,最近幾年它們長得比較好了。接著說他如何用草藥、咒語等治療,但是,當我問那是不是Temuan的傳統時,他否認了。
小時候,有次走路經過一棵香蕉樹,從香蕉樹上跳出一個女人。晚上她來到我的夢裡,問我要不要學Temuan的治療方法—我拒絕了,因為那要遵守很多禁忌,我不想要那種生活。後來我改信伊斯蘭教,有天又夢到一個穿穆斯林衣服的女人,問我要不要學治療病人,我就答應她,所以她會到夢裡教我。
他說他現在混合兩種方式,有些是他小時候看長輩學的Temuan咒語,有些在夢中學的。這故事使我感興趣的,不只是他提到神秘的療法,而是不管是傳統的織法、草藥或治療方法,縱使仍抱怨著現在、懷念著過去,但這些都是他延續生活在Temuan裡的一種方式;因為他的生命經驗加入一些新的身份跟元素,而這些身份與元素也成為他的生存之道。
空白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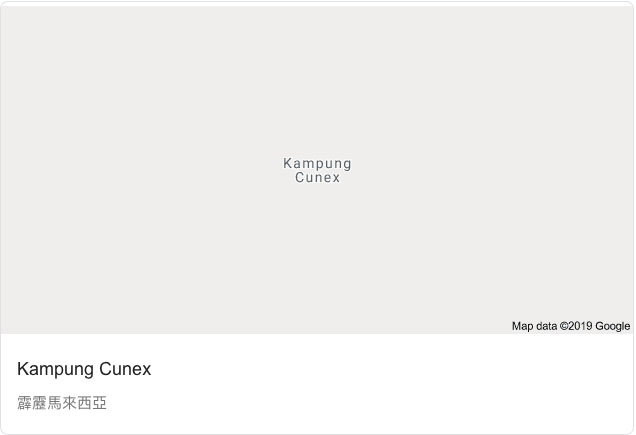
在離開Desa Temuan的路上,Jeffery提起小時候對這區的記憶,他的阿姨就住在附近社區,有時他會跟著家人來阿姨家住幾天,印象中他一直知道這裡有座山,但山裡有什麼,有誰住在那,發生過什麼事,他的家人或阿姨都不知道。
好像你在開車,開著開著開到有叢林的地方就停下來。碰到叢林就像到了盡頭,叢林後方是一片空白。
這種空白也出現在其他時候。比方說,為讓我了解各部落在半島上的相對位置,Jeffery試著在谷歌地圖上幫我查我們要去的各部落位置,但有時候,這些部落在網路地圖或實體地圖上都是一片空白,有時附近沒有商家,有時沒有3D街景服務,甚至沒有標示地名。他會指著特定區域的某片空白說, 就在這個地圖上什麼都沒有、空白的地方。
當然,那裡不是一片空白,並非什麼都沒發生。而在看起來空白的地方所發生的一切,也不會發生在另一個世界 。但考慮到這些地圖是如何被完成的,你就會立刻理解為為何這些地方什麼都沒記錄下來,它似乎揭示在以「國家」為考量的地圖繪製過程中,這些地方是如何遭到噤聲的。
Kampung Cunex:直升機與一顆大石頭
庫內村,Temiar族的部落,屬於上霹靂州。開車上山行經的路面相當顛簸,這原來是伐木商為運木材而開拓的。到訪前,我們透過COAC(Center for Orang Asli Concerns)得知族人正在進行阻擋伐木商進入傳統領域的抗爭,他們設下路障,隨時準備對抗有國家撐腰的財團。庫內村像一個自給自足之地,2016年他們離開政府蓋給他們的大臘RPS(Rancangan Pengumpulan Semula)計劃,決定回到這裡—這個傳說裡「太陽停留的地方」—生活。與其他地方原住民一樣,他們大多經歷二、三次迫遷的生命經驗,祖居地因為政府興建水壩,已被水淹沒。如今他們視庫內村為最後棲地,誓死守護這塊土地。
這是我們停留得最久的部落,在這五天裡,直升機意外地時常被提起。每天大概有二、三次會看到直升機在空中盤旋,偶爾族人會兇狠地朝直升機咆哮。「只要直升機出現一、兩天後,就有伐木商來砍掉一些樹。他們在查看還有哪裡可以伐木。」然而,直升機並不是近幾年才出現在他們生活裡,它還出現在其他部落裡,只是隨著時空改變而有不同影響。
某天我們進森林採集植物途中,族人帶我們到一處較高的空地,地上用白色的石頭拼出部落的名字,下面有大大的「L Z」字母—為了讓直升機清楚地辨識。「還是小孩時,我們看到直升機總是很興奮!」他們侃侃而談著一段直升機有不同功能的時期,在英國殖民期間,曾有醫生會用直升機空投醫療藥物到部落,滿足他們的醫療需求。因此曾經有段時間直升機是友善的象徵。直升機從上空凝視的視野,難免讓人聯想從上方鳥瞰部落,帶有外來者的階級與高傲意味。在攝影語言裡,這種由上往下俯看的鏡頭常在暗示居高臨下的他者凝視。
另一次,族人帶我們走一小段路,去看山溪裡的大石頭,上面有不自然的打磨痕跡,一問之下才知道是過去族人磨刀之處。這種不只是以人為紀錄傳承歷史,而是以地方為主體與自然流變的形成見證。如此互為主體的鏡頭視野,我發現常見於原住民族對待土地的方式。土地上自然/人為的事件痕跡,與我們對待土地的方式息息相關,土地不是物件或承受對象,而是像人和人的互動,透過行為互相影響。我想像,這種觀看比直升機的外部鳥瞰與大面積飄移更細緻緩慢,而非飄浮在雲端。
這很重要,因為這是以前留下的。它讓我們知道以前的人如何生活,這些石頭見證過沒有磨刀石的日子。
但幾天後,我發現另一種鳥瞰。在幾乎收不到訊號的山裡,我將手機丟在一旁,幾天後發現村民還是人人手握智慧型手機。原來離部落不遠的山丘附近,是少數收得到訊號的地方,於是我們跟著青年,拿著手機到山下搜尋網路訊號。山丘上有一整片焚燒過的空地,族人透過焚燒森林的方法使土地更加肥沃而適於耕作。這個地方,可以清楚地俯視整個部落,有集會所、家屋、專門進行儀式的房屋,和耕地。由上往下看,很快就了解族人是如何規劃他們的空間,並思考生活與環境的關係。
我們在山丘上遇到Pam,他是部落裡的行動者,在2016年帶領族人回到庫內村,在這裡恢復他們的傳統宗教儀式,延續祖先在這片土地上的生存方式。同時持續對外聯繫,融合傳統與當代的生活方式,正是他們對抗大舉入侵開發的抗爭方法。我想起家鄉的馬太鞍老頭目對我說的話:「領導者要像老鷹一樣飄在部落上方,用老鷹的眼睛俯視整個部落,看顧整個部落。不只要知道部落發生的每件小事,還要看到完整的模樣。」在爬上山丘的那個黃昏,Pam與幾位部落青年鳥瞰著部落,我們與他們各自聊起與伐木商、政府對抗的理由,它們各有不同想要保護這片森林的原因,凝聚為他們看待部落的共識。雖然這種超我的鳥瞰,在攝影語言裡與直升機凝視看似相同,但其實非常不一樣。
Jeffery和我各自透過影像和照片的鏡頭,也希望從他者的視野裡,經由相紙的顯影與影像的播放,達到如同看待石頭的視野般互為主體的見證。
「在你的故事以前」
既然你對我們的文化和故事也有興趣,我們就這樣一起聊天。一起聊天,一起達成共識,世界也和平。
Atok Long第一次和我們聊天時,這樣對我說。我為他說了馬太鞍部落的起源故事;首先來了大洪水,兩姐弟坐上小船逃難,經歷數次遷徒,才來到現在馬太鞍的老部落。我告訴他這是我們的起源,我們沒有比這個更早的故事了。Atok Long笑著對我說:「我聽完你的故事,現在我要告訴你全部的故事,在你的故事發生以前的故事。然後你的故事就會變完整!」於是我們花一個下午待在他的房子裡,他緩慢地告訴我,他們的世界怎樣被創造出來,身旁的青年不時加入討論或翻譯。
他的故事結尾,正好接在我的故事開頭。
我分享了台灣原住民的殖民經歷與自己的生長經驗。某晚,當我分享完台灣原住民的處境以後,一位族人用馬來文表示他想知道更多,「我覺得聽不夠。然後呢?我想知道更多,我想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因為他覺得那可能是他們的未來,但我無法告訴他這是否他們的未來,或看似無妄的未來中有怎樣的解答。這種交錯的時間感,在這次的旅程中不斷地經歷。在不停反射對方文化脈絡與觸境的過程當中,縱然理解彼此來自差異的殖民脈絡、南島語系的分支語族等等前提,但在因為「原住民族」身份而被納入不同統治階序的國族族群之間,我們得以從對方的處境獲得延續,跨越時空看到自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並以此作為彼此觀看的起點。
「很多馬來西亞人都沒勇氣站起來捍衛自己的歷史,因為遭到政府的壓制。尤其是當他們的歷史與政府的歷史不同的時候。」Atok Long最後告訴我們。
Kampung Jemeri:太簡單的河
過去一直依河而居的Jakon族人,居住在公路旁的Jemeri聚落,而在這個族人的祖居地上,已開發成一座座的棕櫚園。Atok Dobi是部落的耆老,他對萬物靈魂抱持崇敬的心,對傳統儀式總有自己的要求,時常看見他獨自一人跑到旁邊,默默地對空氣講話⋯他總是與地方上的靈魂連結,無論到哪裡,他都先通報地方存在的其他靈魂,這些講究的過程反應出他對於維繫傳統的使命感。於是,從抵達這裡的第一天起,他就不停叨念著讓我們認識他們的河流,每個支流的名字,哪些地方互相交會,以及河裡的靈魂。
由於Atok Dobi日日唸著我們要記錄下河流,於是我們約了某晚,讓他按照記憶把河流畫出來,並請部落青年在一旁聽寫地名。Atok Dobi緩緩在紙上畫線,偶爾閉起眼睛,彷彿他正神遊在河道間,偶爾斟酌每個支流的長度,下筆慎重。一旁幫忙聽寫地名的青年第一次聽見這條河流各區域的名字,他的生活已經離河流非常遙遠。待Atok Dobi畫完河後,我們請其他長者一起討論這張地圖,他們對於不同的支流、過河的方式甚至捷徑,各有不同記憶,開玩笑說這張圖是太簡單的河,但是這張太簡單的河的地圖卻因為各自記憶和互相糾正的過程而立體起來。我想起幾天前Jakon長者對我的教誨:
重點不是原來的地名什麼,重點是你要自己經歷這條河,每個人都可以為這條河發展出自己的地名,每個人都該有自己的地圖。
無論是這次的旅途或我過去的生命經驗,時常會收到族人邀請我們幫忙記錄下他們的文化或故事的要求,他們往往強調這些應該要「寫下來」。由於受到殖民歷史及強勢語族文化入侵的影響,過去沒有文字而僅僅以口述記錄歷史的原住民,總是感受到「寫下來」或記錄在書本裡的急迫性。我總是感覺無論是說故事,地理知識或邊界的認定,口述傳統本身包含關於對象的討論空間,以及隨不同口述時空而增減的創造性。然而,當這樣的文化特性遇到如今人們要求書寫的準確,與對文獻的執迷時,難道只能是無解的矛盾嗎?